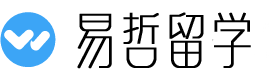【文/里翰·萨拉姆,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埃米·古特曼(Amy Gutmann)是一位知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美国总统乔·拜登派驻德国大使的不二人选。在漫长且硕果累累的学术生涯中,她为协商民主理论、身份政治、教育机构在多元社会中的作用等学术课题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些课题在如今的大西洋两岸都前所未有地重要。考虑到俄乌冲突的大背景,由一位德国犹太难民的女儿在柏林代表美国利益,毫无疑问会引发许多共鸣。
但笔者怀疑,古特曼之所以能够受命担任美国最知名的驻外大使职务之一,并不是因为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跟她的祖籍没什么关系。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拜登总统认为自己欠对方一个人情。相比令人瞠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巨额捐款,古特曼女士给予了总统先生一件更加珍贵的东西。
就任大使之前,古特曼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了18年的校长,她因出色的筹款能力与战略眼光而广受赞誉,并获得了不菲的报酬。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2月,古特曼主持成立了宾大拜登外交与全球参与中心。拜登亲自担任该智库的负责人,他同时也被宾大授予本杰明·富兰克林总统实践教授这一荣誉职位。
图为拜登与古特曼一同出席活动。拜登被授予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职后,宾大录取他的孙女符合在美国精英大学长期通行的“传承录取”模式
让一位前副总统加入你的教职团队可不是一件小事。古特曼似乎与拜登建立了深厚默契。2018年,拜登的孙女梅西·拜登(Maisy Biden)申请报考宾大时,拜登亲自向古特曼说情,后者似乎为增加拜登孙女的录取几率提供了宝贵建议。尽管学术成绩并不出色,梅西还是在2019年秋季被宾大录取,且于今年春季毕业。彼时,古特曼已经完全适应了在柏林的大使生活。
笔者并非是嫉妒拜登采取各种手段为孙女争取到上名牌大学的机会,这种爷爷为孙辈奉献的精神令人钦佩;笔者也不会抱怨古特曼卖了拜登一次人情,毕竟她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宾大的招牌贴金。然而,这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令人十分震惊。一般来说,人们会期待大学校长向前副总统献殷勤,而不是反过来。
然而,古特曼并非一所美国普通大学的校长,她是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校长。这个区别改变了一切。古特曼与拜登家族的关系完美诠释了常春藤盟校及类似高等教育机构的巨大影响力,也预示了这种影响力可能会如何终结。
数十年来,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凭借数十亿美元捐款,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庞大富人阶层的“规范养成者”。通过将权贵子弟与一部分选定的弱势群体子女相结合,这些大学培养出了新一代美国进步主义精英,对整个国家的文化与政治生活拥有巨大影响力。如今,随着常春藤盟校的招生规范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左右翼势力的严格审查,这种行之有效的“炼金术”的命运岌岌可危,也为新一轮精英生产机制打开了大门。
古特曼最杰出的前任之一是前美国驻德大使詹姆斯·布莱恩·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他曾担任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冷战之初的首位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十分巧合的是,柯南特在就任驻德大使这个重要职务前,也做了20年的哈佛大学校长。
詹姆斯·布莱恩·柯南特,美国化学家、前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1933年至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
从柯南特的时代到古特曼的时代,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走向了权势巅峰。然而,柯南特对哈佛的愿景与古特曼对宾大的愿景截然不同。
柯南特的童年是在波士顿一个工人阶级之家度过的。他任哈佛校长期间最知名的举措,便是将这所被视作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精英的养成学校转型成一座更注重择优录取的学府。他责成大学行政人员寻找一套能够选拔出全美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年轻人的考核机制,即日后SAT考试的前身。
柯南特相信,哈佛大学能够推动实现“杰斐逊的理想”:由一群通过了严格且有据可依的选拔机制考验、心系公众的知识分子精英来领导美国。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柯南特们所代表的理念是哈佛及类似高等学府在他们心中地位如此崇高的最有力证明。因此,一旦违背了择优录取的初衷,常春藤盟校在美国民间的精英人设会迅速坍塌。
现实中,这样的择优制精英主义从未完全付诸实施,尤其是在常春藤盟校中。首先,柯南特本人就推行过犹太学生录取配额制,被批评对各种反犹主义措施至少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柯南特时代之后的数十年间,一大批美国大学的管理者放弃了择优制精英主义,转而追求一种更为不同、据说基础更加稳固的精英制。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不再一味强调学术卓越,而是采取了更加多元化的路线,将仅凭学术成绩选拔出来的学生与另一批学生相结合——不管是基于字面意义还是隐喻,这批学生的存在意味着“丰富大学生活的多样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背离了择优制的选拔方式被视作向筹款需求与其他纷繁的机构目标做出妥协。然而,近年来,这种多元化的招生模式被赋予了新的道德内涵。不妨称之为“进步精英主义”(progressive elitism)。
1995年5月,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劳伦斯·S·洛克菲勒政治学教授及系主任的古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知名的人文学科“坦纳人类价值讲座”上发言。她在演讲中强调了种族歧视问题,称之为“美国公共生活中道德和智力层面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古特曼的核心观点之一包括,“能够有效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公共政策与个人实践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黑人批评其他黑人同胞也是公平合理的,因为那些黑人从前者反抗种族歧视的努力中获益,却对这一事业或同样紧迫的其他事业毫无贡献”。也就是说,美国黑人“需要团结起来抗击种族歧视”,比如,支持高等教育中基于种族因素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s)政策。
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对以种族肤色为依据给予特定待遇,但此后推行的“平权法案”却演变成在招聘/招生过程中给予特定族裔优惠
古特曼认为,不仅仅是美国黑人应在这一领域肩负特殊义务。她表示,“我们必须承担的种族负担越少,我们对克服种族歧视的义务就越大”。非黑美国人“尤其肩负抗击种族歧视的特殊任务,这样才能减少他们成为不公平优势获益者的可能性,这些不公平优势起源于社会机制中的种族主义成见或其他形式的制度化不公,它们以有悖公平的方式令黑人群体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古特曼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享有特权的个人或团体肩负特殊义务,需要放弃他们通过不公正手段(这种手段加剧了种族不平等)获得的优势,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拜登总统帮助孙女进入宾大所做的努力?或者说,该如何指望身为政治哲学家的埃米·古特曼来理解这件事呢?
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是,目的决定手段。换句话说,当特权阶层利用自身的地位、人脉和财富来换取高等教育机会时,如果这样做有利于更广泛层面的种族与社会正义事业,则应当被视作合理与恰当的。
身处古特曼这种地位的人可能会坚称,因为她主持的大学正在践行她和同僚们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招收那些能够体现这类价值观重要性以及学校声誉的学生,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追求。对平等主义的承诺不仅赋予了宾大等高等学府一种道德上的通行证,也凸显了一种道义层面的迫切需求,需要通过录取这个国家最具特权家庭的子孙后代来充实他们的学生队伍。由此,以古特曼为代表的“进步派大学校长”拥有了一件能够塑造美国精英后起之秀的重要工具。
最重要的是,这个精英培养计划需要一种接受度更高的合法性理论。如果说,择优制精英主义的正当性源于需要向美国最优秀的人才传授爱国主义与公民责任,那么进步精英主义的正当性则源于实现美国精英的多元化。这意味着增加非裔美国人、其他历史上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族裔群体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代表性,以及保护和加强常春藤盟校扮演机会瓶颈的作用。在进步精英主义的影响下,常春藤盟校不仅仅是老钱精英的后代与第一代奋斗者子女相遇的场所,也是美国精英被打上“道德烙印”的地方。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起诉哈佛大学”案揭示了这种精英培养方式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原告是一个反种族歧视的非盈利性法律支持组织,聘请了杜克大学劳工经济学家彼得·阿西迪亚可诺(Peter Arcidiacono)。他通过研究哈佛多年来拒绝公开、但被迫分享给原告的录取数据,来分析哪些申请者被哈佛录取,哪些被淘汰。阿西迪亚科诺的专家证词揭示: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长期歧视亚裔美国人申请者。这引发了保守派对带有种族偏见的招生活动的批判。阿西迪亚科诺与同事也提请外界关注哈佛大学通过体育生、传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s,指美国大学优先录取校友子女或亲属的合法招生方式,观察者网译注。)、院长利益名单等方式招收学生的偏好,还包括优先照顾教职工的子女,这在部分案例中的比例大得惊人。
今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基于种族因素考虑的招生政策违宪,事实上推翻了在美国实践数十年的“平权法案”政策
阿西迪亚科诺的研究结果令支持与反对基于种族考虑招生的人同时感到震惊,并一致谴责哈佛的ADLCs政策(即前文指的通过体育生、捐赠、传承录取与院长利益名单等方式招收特定学生的做法,观察者网译注。)。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分裂的两拨人能够达成一致的情况十分罕见。本质上来说,基于种族考虑的招生与基于利益输送的招生是互补的,正是这种互补构成了进步精英主义的基石。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精英教育的主要优势不在于教育质量,而在于提供了结识权势人物的人脉。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沙姆斯·欣(Shamus Khan)近期在《纽约时报》发布专栏文章,描述特权阶层学生与非特权阶层学生之间的交往如何令后者获益。
他写道:“从名校毕业会给予你一张进入精英小圈子的门票,与身居高位者身边的人物建立关系,并接受上流阶层规矩与礼仪的熏陶。”然而,那些出身背景优渥的学生在进入哈佛或宾大之前就已经能接触到富裕、受过高等教育、在专业领域成就斐然的成年人关系网络,出身较差的学生却没有这种机会。当这些学生聚在一起的时候,特权学生在智力、成就与品格方面的优势得到认可,而毫无背景的学生则会获得社会与文化资本,能够加速他们在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发展。
虽然欣并不打算为优先录取校友子女亲属的做法辩护,但他注意到,“这些通过传承录取的学生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人脉,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条件较差的学生如何从名校中获得众多好处。”这种逻辑不仅仅适用于校友的子女亲属,也包括其他特权阶层的子女,比如民选高级官员、大慈善家、知名学者与文化界人士,甚至可能是卓有成就的马术或壁球运动员的子女。
进步精英主义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塑造精英大学生的礼仪、风尚与人生轨迹。它还允许招生官员进行更大范围的“灵魂改造”。
2010年,经济学家瓦莱丽·拉米(Valerie Ramey)与加里·拉米(Garey Ramey)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美国名牌大学录取名额的竞争愈演愈烈,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家长投入到子女教育上的时间与资源急剧增加。相比之下,加拿大父母在同样条件下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因为加拿大高等教育中社会地位等级制的影响远不如美国那样大。拉米夫妇的结论是,这样一种剧烈竞争直接导致了浪费资源、零和博弈的“鸡娃竞争”(Rug Rat Race)。
在这种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评论作家马特·费尼(Matt Feeney)更进一步。他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中批判了美国大学选择性招生制度的傲慢,指责招生人员手中的权力过大,冒犯了望子成龙的父母以及他们子女的内心世界。
随着美国“零零后”一代人逐渐成年带来的大学申请人数激增,费尼断定,“招生人员逐渐意识到,这种竞争赋予他们的选择权也是一种深刻且微妙的道德权力……他们现在可以告诉申请者,哪些课外活动更有价值,什么形式的自白在个人陈述文案中更讨喜,以及通过这些课外活动与短文体现出来的哪些个性更容易得到招生官的青睐。”通过向家长、教师、中介以及对任何微小的等级制地位变化高度敏感又焦虑的年轻奋斗者传递这种偏好信号,招生官们发现,“他们可以引导大学申请者成为什么样的人。”
部分学者与教育从业者就呼吁利用美国大学的选拔机制,通过多重手段“影响”家长与学生。比如,2017年,托马斯·斯科特-雷顿(Thomas Schott-Railton)在《耶鲁法学与政策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呼吁精英大学向曾就读于(高贫困率的)K-12公立学校的申请者提供可观的入学补助金,哪怕他们并非来自低收入家庭。他认为,“通过奖励这类申请者,美国大学将能调动全国各地的私人角色来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先不谈利弊,这个提议的确说明了精英高等教育对美国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的庞大影响力。斯科特-雷顿的提议可被看做让常春藤盟校推进一个很可能遭到国会拒绝的政策目标。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达成立法妥协非常困难。赢得大学招生办公室的支持则显得相对更加轻松。
这种规训式的力量带有意识形态特征,而且并不总是那么微妙。2018年,耶鲁大学的一位招生负责人发布声明,向潜在的申请者和已被录取学生保证,如果他们在高中时期因参加要求控枪的社会游行而遭受退学或其他纪律处分,这并不会影响耶鲁在选拔环节对他们的评价。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能进耶鲁的学生,我们期待你们对社会正义问题有充分认识。”假如耶鲁出一份类似的安慰声明,称学校对申请者参与“反堕胎”游行而感到骄傲,可以设想,发布这份声明的招生官会受到什么样的指责。
一批哈佛非裔学生在支持“平权法案”政策的同时,开始抗议大学采取的传承录取模式
结果是,在进步的大学行政人员与招生官操纵下,能够决定年轻人命运的美国精英大学招生程序,已经异化成一种将进步主义理念转化为精英社会规范的工具。
这自然引出了常春藤盟校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可能已经在走下坡路的原因。
如果说,进步的精英主义让一小部分精英大学在道德层面的进步主义与他们所期盼的精英主义间达成了和解,那么,当常春藤盟校招生官重塑社会规范的权力不再以种族正义为诉求时,又会发生什么呢?自从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判决限制了种族偏好,加上拜登政府宣布对哈佛的传承录取模式开展民权调查以来,这一做法便开始遭受猛烈抨击。阿默斯特学院于2021年10月放弃了传承录取的做法,维思大学今年7月宣布跟进。如果沙姆斯·欣的观点是正确的,当传承录取的模式终结后,就算精英教育对毫无背景学生的象征性价值还能存在,其作为社会和文化资本来源的价值也将大大缩水。
反过来,这将为另一种致力于实现不同价值观的高等教育机构创造机会——甚至可能复兴上世纪中叶对美国精英教育的愿景:促进社会向上流动性,向年轻人传授爱国主义与公民责任感。
而那种愿景,至少是当前美国红州和紫州(即摇摆州,观察者网译注。)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措施背后的动力,这些地方的许多选民、州政府官员与慈善人士都对常春藤盟校所代表的进步主义心怀芥蒂。在公立研究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该校的公民与经济思想和领导力学院近年的招生人数激增。在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Bill Lee)正通过州立大学系统创办一个类似的教育机构,旨在向学生教授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
此外,还有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的汉密尔顿古典与公民教育中心,这是由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目前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执教的威尔·英伯登(Will Inboden)新发起的机构。佛罗里达大学在盖恩斯维尔校区拥有超过6万名学生,已经成为全美最受尊敬的公立大学之一。随着“阳光之州”经济与人口的快速扩张,这所大学的发展前景十分光明。设立汉密尔顿中心的目的是促进多元化思想、提升全校乃至全州的公民教育质量,也是在押宝佛罗里达大学的巨大潜力。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汉密尔顿中心将为创建一所全新的文理学院提供土壤,它将能与宾大或哈佛等名校竞争,吸引来自不同社会与种族背景、聪明能干的学生。迄今为止,佛罗里达大学还没有在推动社会阶层流动性方面发挥出“灯塔”的作用。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改变。
没有人指望这些刚刚起步的努力能够动摇常春藤盟校及其同行处在美国高等教育金字塔尖的地位,至少现在还不可能。但能够确定的是,许多年轻美国人与他们的家庭正在寻找我们所熟知的精英高等教育的替代品,越来越多的有志公民希望重振那些依然在远方回响的择优主义理想。
(原文于8月12日发布在《大西洋周刊》,原标题:“进步精英主义的终结?” The End of Progressive Elitism?)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删文请联系管理员。发布者:admin,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blerks.com/243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