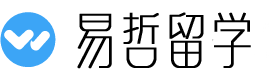◆卓南生
但是,事实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看法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
1984年春天,重返日本小住的笔者发现一个现象:在东京大学的校园里,从未看到一个穿校服的大学生。最初笔者还以为是因为天气转暖,校服过于温暖的缘故,经过和不少朋友闲谈,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再爱穿校服了。一般的大学生是如此,名校生也不例外。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大学生爱读的杂志,已经不再是《朝日新闻》发行的,被认为是革新派的《朝日ジャーナル》,即《朝日杂志》和岩波书店出版的《世界》月刊(不少大学生向笔者表示,这些刊物的内容太枯燥、不易读懂),而是大型的连环图书及讲究衣着及如何追求异性朋友等图文并茂的新刊物。据说,大胆谈论性问题的女性杂志,不仅在女学生中畅销,也受男学生们的欢迎。
不在乎读什么学科
谈到大学生的求学精神与态度,一位大学教授向笔者表示:“现在的学生进大学,不像过去那样认真,有着一定的抱负和期待。许多学生只是想拿个学位,以便进一间大公司罢了。至于在大学能学些什么或应该学些什么,他们不加思考,也无所谓的。”
基于此,据说许多学生在没有投考大学时,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要选择哪一系。他(她)们可能在甲校投考A学科,到乙校则投考相去一万八千里的B 学科。总之,只要能进某一流的大学即可。
尤其令笔者当时惊叹不已的是,“大学校园祭”(即文化节期间开放给公众人士的庆祝活动)已不再是学术成绩展示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而是充满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在相对上,严肃的演讲、讨论的活动大大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斥整个校园的“炒面摊子”和介绍异性朋友的“恋人研究会”。
高中生的思考方式
询以学生主办“炒面摊子”及“恋人研究会”的目的,大多数的回答是为了好玩和凑热闹,但也有不少坦率承认目的是为了“赚钱”,以便在假期去旅行。
针对大学生气质的蜕变,笔者曾四处探访,一位社会学学者的看法是:“他(她)们的个子虽然高大,但思考能力却与过去的高中生无异。”
一位日本官员则私下表示:5、60年代,是学生充满“梦想”的时代,他们爱思考、重视集体的力量。但是,7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大学生已经再也没有了“梦”,他们不看未来,也不想过去,只是重视今日的个人享受。
谈起20世纪60年代日本大学生满怀着“梦”与强烈的求知欲,笔者是有着深刻的感受的。在笔者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学潮频繁的时代。由于学潮而停课是常有的事,再加上日本的大学教授们似乎都得了“休讲”的流行病(在大学的日语教材中,很早就出现“休讲”的课文,因此尽管中文没有这个词汇,但学生谁也都记牢,因为它很“实用”),学生们从课堂中所学到的东西并不多。虽然如此,笔者所认识的不少大学生并不因此而放松自己的学习。一名文科大学生就曾经向笔者发出如此壮语,他要强制自己每个星期看完两本岩波等书店面向大学生的普及版丛书(如“岩波新书”系列、“讲谈新书”系列等),尽量吸收各方面的知识。
日本大学生如此勤学的精神,笔者在后来所住的一间日本学生与留学生合住的宿舍里,也有深刻的体会。根据该宿舍规定,留学生与日本人合住一房。笔者习惯于早睡,因此被分配睡于双层床之上层,而同房的日本朋友据说是有迟睡的习惯,他表示要在房灯熄灭之后继续在床上看书。最初,笔者还以为所谓迟睡,再迟也不过是夜间一点两点,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兄的迟睡,其实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的。同样是使用汉字,“彻夜”二字在日本如此普遍地挂在学生口上而成为日常用语。在新加坡,偶尔也有同学“开夜车”,那大抵上是为了应付学校的考试。一般不被认为是健康的现象,而被视为“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结果。但环顾当时日本朋友之所以“彻夜”,却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笔者对此不能不感到钦佩(当然,日本学生之所以能够耐得起“彻夜”之煎熬,也许是与高校时为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被迫少睡之训练有关。)
不再彻夜读书与谈哲学
勤劳的日本学生为什么非“彻夜”不可呢?笔者曾仔细观察。答案之一是一部分学生白天都在忙着搞学生运动,而大部分学生白天都得为学费与生活费而操劳。“兼职”,几乎可以说是日本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日本苦学生或者半工半读学生如此普及,这对于当时的留学生来说,不能不感到吃惊。在当时的新加坡,半工半读的大学生固然有之,但为数不多。至于到海外留学的学生,除了一小部分是奖学金学生之外,大部分都是来自家境较佳的家庭。因此,在相对上,当时真正半工半读的学生并不多见。
记得当年有一两名同学曾经当过一个时期的“新闻少年”,每天冒着风雨派报,然后才整装上学,在留学生界传为美谈。大家都敬仰其刻苦勤学的精神。反观日本的大学生,除了一部分当家庭教师,从事粗重体力劳动的也为数不少。尤其令笔者深感钦佩的是,不少家境不错的日本学生(甚至是社长的孩子)也半工半读,这在新加坡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
想起当年日本苦学生或半工半读学生人数之众多与对工作之毫不挑剔,再看看今日留学生(指真正的苦学生)之遭遇,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生的缩影。从这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前些时候日本大众传媒大事渲染的“留学生可怜论”,甚至将他们作为“难民”看待,显然是患了“健忘症”。对于真正苦学的半工半读学生,不管是日本大学生或留学生,同情与鼓励是需要的,但决不是以可怜的姿态予以施舍。这只要处身置地着想,其理至明。
大学生认真、严肃、关心政治和爱谈哲理,这是笔者留学时代的另一个日本大学生的形象。撇开每天拿着麦克风发表演说与游行的活动家不谈,一般的学生聚在一起,也常常围绕着时局问题高谈阔论。当然,有时也难免争辩得面红耳赤,甚至是不欢而散。在笔者所住宿舍的食堂里,就常可看到或听到大学生之间激烈的争辩,听听彼此争辩之论点与立场,倒也是了解当时日本青年之看法与苦恼之一良好途径。
也在同一间宿舍,笔者首次领教了日本式又长又无生产性的会议的味道。不知道今日新人类学生开会的方式是否已经改变,但在当时对于留学生来说,“寮会”(全体住宿生的定期会议)确是再乏味不过的事。它之所以枯燥无味,一来是讨论议题不明确;二来是日本式的会议讲求满场一致。加之那是一个大学生爱谈哲学、理论的时代,如果碰到一个可以争论的课题,那准会争个天翻地覆而不罢休。但现在回头一想,撇开寮会会议方式是否有生产力问题不谈,当时,爱争论的纯朴的大学生,倒有其可爱之处。这俨然与今日追逐名牌货与时髦,懒于思考的青年,是有天渊之别的。(作者系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删文请联系管理员。发布者:admin,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blerks.com/24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