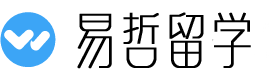时隔三年,人们重新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出行自由,出国游历、求学或定居也重新提上了许多人的日程计划。
一边是国内高考的激烈竞争与内卷的就业困境,一边是网上展现出的美好海外生活,人们跃跃欲试着,想知道换一种空气、换一种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但有条件有机会离开本土的人始终是少数,就像人们朋友圈永远只秀出自己最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内心的辛酸苦涩只对极少人诉说那样,大多数人也只能隔着道听途说、隔着大小屏幕了解中国人在海外的生存状况。
看一面镜子久了,便会以为它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一旦打破镜面,我们才会惊觉它只是一种接近真实但不完全真实的影子。而在镜子的裂缝间,藏着的是被刻意忽视、被试图忘却、却难以弥合的刺痛伤疤。
90后作家蒋在的短篇小说集《飞往温哥华》,便以她本人丰富的异国生存经验为根基,打破了那面虚拟之镜,试图用虚构的故事作为伸向真实的触角,去抚慰被困在镜子裂缝深处的人们。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在同名短篇《飞往温哥华》里,蒋在首先关注的是留学生家庭。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比父辈们更为优越,出国留学也成为了一件更为触手可及的事,每天都有无数的跨国航班运载着人们的欢乐与忧愁,社交媒体里满天飞的留学广告与IP定位在海外的风景照片也令人心驰神往。
我们这一代人的留学生活看上去似乎会更体面、更好过一点。但在艳羡与幻想之前,可以先停一停,听听蒋在怎么说。
身边所听到的留学故事,大多是中产家庭的“镀金”游戏:年轻的孩子被家人安排在国外呆上几年,或是逃离高考的竞争压力,或是洗刷不太理想的第一学历,来为自己争取未来的优势。
但在不太被关注到的角落,仍有许多并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挣一个更好的前程,即使倾其所有也要供孩子到国外读大学。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孩子,也不得不面对着经济上的困顿与背井离乡的孤独。
蒋在真实地记录了这种无奈:故事中的儿子已在国外留学9年,正在准备读博士,看上去一切都在开往成功的轨道上顺利运行,前途不可限量。
但来到温哥华与儿子相聚后,母亲才了解到孩子隔着大洋的电话中被隐去的种种无奈:害怕高昂的酒店费用,在找到住所之前只能暂住半地下室;不舍得花钱理发,于是用发箍整理长长的刘海;不好意思总是蹭同学的车,只得每天走两个小时的路购买生活用品;为了挣一点生活费,每天风雨无阻地跑很远的路给中国人补习英语……
独在异乡的孤独像虫子一样蚕食啃咬着他,抑郁症与焦虑症像蛛网困住了他,但对懂事的孩子而言,报喜不报忧似乎是一种尽孝的方式。
而到了他扛不住压力向母亲呼唤爱时,他也没有得偿所愿:母亲没有为他停留,她只能暂停工作,暂停新家庭,来暂时关照这个被抛到过去、抛到异国的儿子。
苦总会熬过去的,我们都是这么吃苦过来的。她一遍遍对自己洗脑,却无视了孩子对爱的渴求。拼命送儿子出国,换来的是她眼中的不孝,他眼中的抛弃。这类互相埋怨、互相亏欠的故事,也许还会不停上演着。
在母子交谈的背景中,也提到了儿子另一个同学的留学梦——他的家境更为拮据,他只能全靠自己努力获得的奖学金出国。为了实现移民的愿望,他一毕业就开始工作,先是在工地搬砖头,后来进入了还有前景可言的计算机行业。
为了让孩子不留退路,寄到大洋彼岸的家书上也只是写着:“不必挂念,不必多联系,也不必回来……”我们不禁提问,在这些近乎残忍、不惜割舍父母亲情的嘱托背后,一个家庭孤注一掷的努力是否真的能争取到更好的明天。
对国外更为优越的物质文明的向往,是一代又一代移民者不远千里奔赴海外最主流的理由。
二三十年前,移民者如何靠刷盘子、学理发艰难创业的传奇故事疯狂流传,《北京人在纽约》《别了,温哥华》等影视剧也在讲述着移民者如何实现梦想、如何解决又重新陷入生活的一地鸡毛。
到了现在,在已有的生活水平基础上,追寻海外更为轻松自由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全民性的移民浪潮退却后,移民家庭也不再是大小屏幕重点关注的对象。
他们的生活光景有比以前更好吗?或许也不是全部。
《遗产》一篇,移民者一家的故事便是在电视台不断重播《别了,温哥华》的背景音中徐徐展开的——黄杰明的母亲到温哥华第一天,站在住所进门处的那面镜子前照了又照。
她说,国外的镜子是要比国内的亮些,就像她幻想中国外更圆的月亮一样。可惜,月有阴晴圆缺,圆月不一定愿意照耀着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她也不得不放弃热爱的舞蹈,在温哥华做着在她看来毫无尊严的清洁工作。
后来,她哭诉着自己的境遇,埋怨把自己“骗”到温哥华来的丈夫,先来一步的丈夫从不说的那些苦给了她错误的幻想。
丈夫无法劝慰她,只能一遍遍地告诉她,等到了下一代,一切都会有所好转,但真相却是下一代也继承了母亲对他的埋怨。
他们的儿子黄杰明并没有出人头地,只能和女友挤在一间火车站旁的闷热出租屋里,不得不靠工地上没有劳动保障、工作环境恶劣的体力劳动养活自己。
他梦想着做建筑设计师,可收藏的建筑画册只能被一遍遍积灰又一遍遍擦拭;怀孕的女友不断畅想着两人理想的未来,却不知道能不能负担得起又一个小生命。
父亲死后,黄杰明跨越千山万水去领他留在另一个城市的遗产,一路上黄杰明都陶醉在幻想中钱币的叮当响声里,可最后他得到的只有一辆他童年时曾向往的红色吉普车,它尴尬地待在仓库里,开不向理想的未来,也开不往温馨的过去。
在族裔、阶级等结构性压力之下,徒劳地等待“下一代”实在很难成为突破困境的方式。是与父辈重蹈覆辙,还是驾车驶往移民虚拟现实游戏的边境,成为故事悬而未决的疑问。
被故土所驱逐又融不进异乡的尴尬也在跨国亲密关系中淋漓尽致地呈现。
《再来一次》写到一对分离的异国情侣对挽回关系、重新开始的尝试,而两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又与他们背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文化隔阂让中国女子始终无法受到西方家庭的接纳,而回国照顾生病母亲或留在美国与男友生活的两难选择又将她不断撕扯。
在《小茉莉》里,作者关怀着情况更为复杂的异国重组家庭。
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令女子感到格格不入,她认为自己是所有人的次等选择,是丈夫前妻、继女生母的替代品,而她想要的一切都被另一个女人理所当然地夺走。
甚至在纯真的孩子面前,她也无法抑制地感到自卑:“她的同学和父母们转过头看我们,他们能感知到她身世的不幸——不然父亲怎么会再娶一个中国人给她做后母?”
当然,蒋在的写作绝不是局限在“异域”的标签里,她也书写童年,书写90一代独生子女的本土故事。
《等风来》基于作者本人童年经历的创作,在破碎的梦背后是孩子对身边失控事物的无能为力,是对大人们拼命呼喊却无人倾听也无人在意的诉求,大概每个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都会有类似的体会。
《午后,我们说了什么》则是以作者的密友为原型,这个涂口红、翘兰花指的男孩是生活里不太常见的边缘人物,却依然有着我们这一代人典型的生命体验:父母竭尽全力为自己“摆平”各种难题,却不能弥补爱与陪伴的缺失。
11岁开始写诗,18岁开始创作小说。首部小说集《街区那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首部诗集《又一个春天》入选第36届青春诗会诗丛。《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得主……在这些灿烂的履历和光环的背后,蒋在想要的或许很简单:
用文字这把轻轻的羽毛,温柔地拂去伤痕缝隙中的玻璃碎屑,再为被时光辜负的人们留下重若千钧的记录。
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得主蒋在作品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故事以及
千禧一代成长心灵秘史
我们还有这些活动
-End-
2023.6.23
编辑:Yoyo | 审核:Cellur
扫码报名
点「在看」,给阿信加鸡腿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删文请联系管理员。发布者:admin,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blerks.com/15489.html